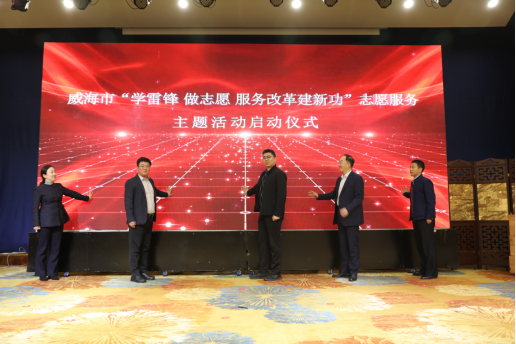运河驿站诗与明清社会文化———以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为例
2024-11-26 17:08 海报新闻
京杭大运河沿岸社会经济发达、自然风光秀美、民俗风情灿烂,可以说是文学艺术的摇篮。至明代,京杭大运河繁荣发展,使得运河驿站成为政客、商贾、文人士子的集散地,同时以运河驿站为阵地,大量运河驿站诗问世。这些诗作或咏物或抒情,构筑起一个独特而精彩的诗歌世界。在运河驿站诗中,题壁诗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元白二人的题壁唱和是古代驿站题壁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同时反映了历史上题壁诗的流行与传播。明清两代,在题壁诗中女子题壁诗最为亮眼,成为反映明清社会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这可以从会稽女子题作于新嘉驿驿壁的诗作中管窥一二。
一、关于新嘉驿女子题壁诗
明万历年间,一名嫁于“燕客”为妾且饱受正妻欺辱的会稽女子作绝句三首题于新嘉驿(位于今济宁市兖州区内)驿壁之上,言词动人,故事凄婉。这便是新嘉驿女子题壁诗的由来。诗共三首,有序于前。
(序)余生长会稽,幼攻书史,年方及笄,适于燕客。嗟林下之风致,事腹负之将军,加以河东狮子,日吼数声。今早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鞭箠乱下,辱等奴婢,余气溢填胸,几不能起。嗟乎!余笼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没无闻,故忍死须臾,候同类睡熟,窃至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并序出豦。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
(其一)银红衫子半蒙尘,一盏孤灯伴此身。恰似梨花经雨后,可怜零落不成春。
(其二)终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无意,留与风流作话头。
(其三)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从序文看,会稽女子是谁名何今已无从可考,但她的身世背景可略知一二。她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长在江南,才情满腹,可惜错付无情将军,身为妾室,日日受压于正妻,如同奴婢,尊严被践踏,身心遭蹂躏。孤独无助的她平日里只得把苦楚埋在心底,强颜欢笑。然而,一日随夫出行至新嘉驿站时,她再次被正妻施以鞭刑,羞愧、愤气填胸之余,为觅知音,以泪和墨,题绝句三首于驿壁之上。
三首绝句字字流泪,声声泣血。“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会稽女子实乃凝泪成诗。全诗反映出旧时代薄命女子的凄惨命运———身具才情却无人可诉、错付郎君且备受虐待的凄婉一生。她于驿壁写下这三首绝句,不仅是对于内心愁闷的自我宣泄,也是对后人能理解自己的希冀,甚至可以说是对当时女性的无声代言,对残酷社会现实的无情抨击。
合山究言此题壁诗为“明末清初最有名的女子题壁诗”,称作者会稽女子为“薄命佳人”,其凄惨遭遇极易与时人共鸣。孟光全、胡俊林从传播学角度将此题壁诗归属为传播学中的“文字传播”,把会稽女子的写诗意图称之为“召唤式”倾诉,是对“知音”的期盼。王勇则细考此题壁诗的后世之传播,究明目前所见的明人新嘉驿题咏、唱和诗涉及作家有20余人,其中除男性文人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女性,直言会稽女子题壁诗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从其故事内容来看,自由被禁锢,尊严被践踏;从其表现手法来看,直抒胸臆,寓情于景;从其传播扩散来看,和者众多,影响深远。一定意义上,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不仅仅是一名女子表达不幸情感遭遇的个人呐喊,而是衍变成一传十十传百的情感共鸣,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而是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学群体———“新嘉驿站文学”。可以说,新嘉驿女子题壁诗反映了明清两代一部分女子的命运,影响甚至带动了一段时期的文学发展,是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缩影,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女子“北上”———动荡中的薄命红颜
会稽女子“生长会稽”,却“适于燕客”,映射了明末清初江南女子“北上”的社会现实。会稽女子身世不详,是如何从江南辗转来到北方也不为人知。并且,是与丈夫结识后来到燕京还是结识前就已经来到燕京,更没有丝毫交代,那么,会稽女子是如何“北上”来京的呢?明代社会动荡不安,逃难流亡而北上的女子很多。所以,会稽女子也极有可能是逃难或是被掠流亡来京。
关于明清江南女子流亡“北上”的故事很多。明弘光西宫才人叶子眉就曾在清兵攻陷南京时被掳掠北上,开始一段苦难的流亡生涯。叶子眉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琴棋书画,皆有造诣,尤以琵琶出众。她且善于笔墨,常提笔作诗,诗意悠远不问世俗。她流亡北上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时曾作题壁诗一首:“马足飞尘到鬓边,伤心羞整旧花钿。回头难忆宫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诗前序云:“马上琵琶,逐尘远去,逆旅过此,和泪濡毫,促装心乱,语不成章,非敢言文,惟幸梓里人见之,知浮萍之所归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婉之情。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女子作为弱势群体在战争中饱受蹂躏,或流亡、或逃难、或远嫁的女子增多。她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常不堪重负,大多因此殒命。刘正刚、王强论述到,“一些妇女被迫到‘婆子营’充当妓女,提供性服务,并‘置队长,监以贼目,而收其值给军用’。这样的惨剧在江阴、扬州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广大妇女除被迫供军队发泄淫威外,有时还被役为守营或苦力。”马国云论述到:“明末清初,一大批女性被迫离开传统的生活空间,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女性的‘流亡诗歌’体现了她们在特殊的生命状态下的思想诉求和情感渴望,她们把贞节视为第一要义,以生命进行抗争和控诉……”。这些被掠北上的女子沦为俘虏、女奴,身心遭受蹂躏却无力反抗,无奈之余,也只能将满腹情愫题于旅壁,以求共鸣。
无论是流亡的叶子眉还是本文所论的会稽女子,都是作诗题壁来表达对内心压抑情感的悲愤宣泄。会稽女子与在流亡逃亡途中殒命的江南女子是不同的,最终嫁给了“燕京”的丈夫,由此摆脱了战乱动荡。但是,会稽女子“薄命红颜”的命运却没有改变,她只不过是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逃亡———不幸的婚姻。
无独有偶,会稽女子“适于燕客”的婚嫁经历与清代著名才女王端淑有相似之处。王端淑今浙江绍兴人,也如会稽女子一般北上远嫁,曾作诗《北上》:“十五习女红,十六离闺阁。远嫁去燕京,父母恩情薄。”王端淑是明代著名学者王思任的第三女,自幼饱读史书,满腹才华,后嫁于燕京的丁圣肇。从《北上》一诗来看,王端淑在十六岁时远嫁燕京,离家北上,但也有人考证她是在与丈夫结婚两年后才随夫北上还京。王端淑嫁为正妻,会稽女子卑为妾室,相似的北上远嫁,不同的身份地位,注定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三、流落才妓———会稽女子的身世之谜
承前所述,江南才女王端淑嫁于“燕京”丈夫丁圣肇。丁圣肇虽担任军前监纪但性情疏散;王端淑虽是诗情满腹的江南女子,但却具“丈夫气”。夫妻二人性格迥异,形成鲜明对比。关于王端淑与其丈夫的关系,王鹤曾写到,“在人际关系中,王端淑是这个家庭当仁不让的主角,对于丁圣肇的依附地位,师友们也都习以为常。”由此可见,王端淑在其夫家有着较高的地位。
会稽女子与王端淑虽然同样是北上远嫁,“适于燕客”,但婚后却是一个地位卓越,一个则卑微到了极点。闺秀出身的王端淑嫁为正妻,婚后仍可嗜书史,工笔墨,不事女红,甚至为丈夫张罗妾室。相较之下,同样“幼攻书史”的会稽女子却只能委身妾室,不仅不受丈夫待见,还要遭受正妻欺凌。这难免让人猜想到她的出身极有可能是一名“才妓”。
所谓才妓,置身青楼,以艺娱人,其职业的特殊性造就了她们多才多艺的本领,往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造诣非凡。若会稽女子果真“才妓”出身,那么其虽才高却嫁作人妾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载的自汉魏六朝至今的四千多名女性作家中明清时期就占了九成之多,而才妓占据其一席之地,是明清才女的典型代表。才妓群体的出现,可以从当时“养瘦马”的江南风俗略窥一斑。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所谓“养瘦马”是指青楼买来幼女,教以歌舞书画,待其成年后再高价卖出,从中谋利。而这些所谓的“瘦马”长成后多被卖于富贵人家为妾。李渔在《风筝误·贺岁》中所写“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就表达了当时社会对于“才女”的审美需求。
对于才女的审美需求,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女子教育。才妓自幼识文断字,以诗文陶冶情操,成为当时才女的代表。一身才情同样也造就了这些女子超前的“自我觉醒”,她们往往追求人格独立,行为举止也与世俗礼教常有悖离。可以说,明清女子教育有其矛盾性———封建礼教之下,女子游走在“才华横溢”与“无才是德”的拉扯之中。于洋以《红楼梦》中女子为例论述到,“贾府里的女子教育并不纯粹,它没有完全冲破明清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正统规训,年轻女性犹如在‘德’与‘才’之间走钢丝。”女子追求独立人格的“志向”与封建礼教宣扬的“女德”水火不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子虽才高但命薄的命运,实乃可叹。
四、题壁盛行———女性文学的繁荣之象
新嘉驿女子题壁诗出现之时,正值中国历史上女性文学和女性题壁诗开始繁荣之际。新嘉驿女子题壁诗备受时人关注,说明对女性及女性文学的关注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新风尚。
关于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陈秀玲论述到,“与当时社会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女性自身觉悟的唤醒都是密不可分的”,女性作家的觉悟被唤醒,表现为“女性对文学创作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不仅创作热情激增,而且其发展有家族化趋势”,“女性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结集、刻印”。结集说明诗作之众,刻印则说明欣赏需求之高。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繁荣,可谓壮观。基于此,女子题壁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一批代表性的女子题壁诗问世之外,与之相关的和诗也大量涌现,直接带动了当时诗坛的活跃与兴奋。
曾为明弘光宫女的秦淮女子宋蕙湘在十四岁时被虏入军,行至汲县(今河南卫辉)时,题壁作诗四首,诗曰:“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别故庐。谁散千金同孟德,镶黄旗下救文姝。(其四)”讲述了她十四五岁被迫离开家乡给胡人做妻,祈求有人能够像曹孟德一样豪侠仗义,把自己从镶黄旗下救赎出来。这首题壁诗可谓是宋蕙湘被乱兵所掠之时的一封“求助信”。明代诗人张煌言作诗以和,“猎火横江铁骑催,六朝锁钥一时开。玉颜空作琵琶怨,谁教明妃出塞来。”表达对宋蕙湘等被掠流亡女子蒙难的同情和对动乱社会的抨击。
清人王素音,在清顺治年间被乱兵所掠,流亡至冀北时在良乡琉瑠河(今北京市郊)的馆舍墙壁上作诗三首并序,诗曰:“多慧多魔欲问天,此身已判入黄泉。可怜魂魄无归处,应向枝头化杜鹃。(其三)”她在诗序中写到,“妾生长江南,摧颓冀北。……事已如斯,因夜梦之迷离,寄朝吟之哀怨。嗟乎!……敢薄世上少奇男,窃望图之,应有侠心怜弱质。”从序、诗来看,王素音的题壁诗情辞哀凄愤惋,一时和者甚众,王士禛就在《过长沙道中见妇人题字用其意作韵》中和道:“离愁满眼,日落长沙秋色远。湘竹湘花,肠断南云是妾家。掩啼空驿,魂化杜鹃无气力。乡思难裁,楚女楼空楚雁来。”王士禛“魂化杜鹃无气力”,既是在共鸣魂向杜鹃的王素音,也是在抒发自身离乡思乡的惆怅之感。
题壁诗不单单是个人的抒情诗,更是一个群体的共鸣诗,这点可以从大量的和诗中看出,宋蕙湘和王素音的题壁诗,均有和诗出现,且数量较多,本文所论的新嘉驿女子题壁诗的和者更是多达20余人。那么,女子题壁诗为何会有如此魅力呢?“怀才不遇的男性诗人,对与自己有着相似不幸人生的薄命佳人的命运,极易产生共鸣和同情”,合山究的论述切中肯綮。
明末清初的女子题壁诗,反映了动乱时代以自身不幸遭遇痛诉战乱的“难妇”“难女”的离家之悲、流亡之苦,诗中尽是被乱兵所掠辗转于驿舍的悲恨以及流落天涯的辛酸。
值得一提的是,会稽女子的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与上述被掠的“难妇”“难女”的题壁诗有所不同,它代表了另一种女子题壁诗的类型———“遇人不淑”,“所适非偶”。这种反映不幸情感遭遇的题壁诗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所以,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一被发现,就引起时人关注,被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和同命相连的女子争相唱和。
明天启初年,诗人袁中道和钱谦益在北上途中发现了这组题在新嘉驿驿壁上的诗文,感其悲切,作诗以和,表达了对会稽女子的惋惜之情,使得会稽女子的新嘉驿题壁诗广为流传,和诗频出,一时间不知名的新嘉驿也成为有名的“文学圣地”。对新嘉驿女子题壁诗进行唱和的诗人,除男性之外还有一些女性。明代女子柔嘉就曾作诗《和会稽女子》,诗曰:“憔悴天涯对阿谁,若为多露独含悲。空怜子夜孤亭泪,尽作霜枫带雨垂。”同是天涯沦落人,柔嘉对于会稽女子的不幸遭遇深有同感,她想象着会稽女子驿壁题诗,不免孤亭落泪,连带着霜打的晚枫都跟着悲泣起来。
在康熙之后的清代,反映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的题壁诗被“伤感怀古、赏花观景、隐匿闲适以及个人失意的述怀所取代”。与此同时,新嘉驿女子题壁诗这种直抒不幸情感遭遇的题壁诗倾向,几乎成为女子题壁诗的一般特征。如清代女子白浣月在任邱(今河北沧州)旅店题壁作诗,在诗序中写到“妾白浣月,家住半塘。幼失双亲,寄养他姓。……岂意生命不辰,所适非偶。……余爰题之驿壁,人共怜之黄土可耳。”作诗云:“新诗和泪写邮亭,珍重寒宵谁面壁”,表达了自己不愿强为远嫁但又无能为力的悔恨与悲愤之情。如此种种,都表明这一时期女子题壁诗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文坛女性文学的繁荣之象。
五、文人云聚———驿站成为文学“交流场”
驿站负有传递公文、转运官物、接待来往官员等职能,其主要建筑是“驿馆”,此外还有驿厩、驿库、驿厅等。“驿馆”又称“馆驿”,类似称谓在当时还有“邮亭”“邮舍”“传舍”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有时为了传递紧急公文往往需要健卒快马日夜兼程,官员的升迁赴任等也动辄就需要数月行程,而驿站就是官方设立的“接待站”。
刘广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邮亭诗抄》辑录了魏晋至清末的1000首诗篇,基本是一驿一诗,既在谈“诗”又在写“驿”。书中介绍了历代邮亭、驿、站、馆、台、铺780余处和500多位作者,可谓驿站所在,文人云聚,诗作繁生。“邮亭驿舍又是诗人题壁留诗的地方。诗人的一些作品(不单是邮亭诗)正是通过这个‘窗口’和‘走廊’传向四面八方。请看古代诗人笔下的描绘:‘行人旧题诗满墙’,‘行役诗篇满墙题’……‘驿壁题诗’也是当时诗人抒发才情、交流作品的一种方式”。刘广生不仅提到了题壁诗,而且对驿站的功能、定位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由此可见,驿站在文学交流史上起到了推动作品创作、人文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嘉驿女子题壁诗所在的新嘉驿位于山东兖州府滋阳县境内(今兖州市新驿镇新驿村)。新嘉驿站是一大型驿站,客流频繁。清光绪十二年修《滋阳县志》卷一《建置志·异传》中记载:“滋阳为齐鲁襟要,南北通衢。凡三江二浙、七闽五管,岁时朝贡,皆由此取道而北;其皇华使节,有事于下国者,亦往往由此取道而南。故邮政宜亟讲焉。”境内新嘉驿为“明洪武二十九年添设”,“行馆最为华整”。
明代文人王韦途径新嘉驿偶遇旧友,作诗《新嘉驿遇顾九和》:“下马邮亭若有期,南还北去各凄其。殷勤野老来相馈,邂逅壶浆坐不辞。雪满郊园埋宿草,风吹林麓堕寒枝。十年离索惊回首,却恨逢君是路歧。”表达了对旧友的依依惜别之情。明代书法家、文学家黄汝亨作诗《新嘉驿亭》,描写了秋天的新嘉驿,“结阴深驿舍,即与世喧分。小涧偏沈日,孤亭亦贮云。藤萝秋与寂,林响暮还闻。不觉移时坐,衔杯半入醺。”明代大臣屠侨刻画夏季新嘉驿草亭写到,“草堂依传舍,幽事坐中新。水曲池通井,花繁夏续春。风尘为客倦,泉石寄亲情。杯酒双蓬鬓,乾坤此是真。”明代马世奇颇有文名,过新嘉驿时作诗《雨后饭兖州新嘉驿》,“征尘初得雨,客路适过中。小憩怜驺力,微凉慰酒筒。官亭幽自好,驿树午还风。饭罢一林眺,凄然念二东。”以雨后“微凉”表达内心凄然之感。像这样写景抒情的诗作,不胜枚举。
如前所述,会稽女子题壁诗使得新嘉驿站成为有名的“文学圣地”。明末清初的文人(包括题壁诗的读者和诗文唱和者),或亲临新嘉驿品读诗作,或间接耳闻会稽女子题壁事迹写诗以和,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学群体———“新嘉驿站文学”,带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新嘉驿这座“驿站”成为当时文学乃至社会人文交流的“聚焦点”,可谓是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交流场”。
前述明人新嘉驿题咏、唱和诗涉及作家20余人,既有袁中道、钱谦益等男性文人写诗以表赞美之情,也有柔嘉、畹兰女士、长春姐等知识女性唱和抒发共鸣之感。袁中道和钱谦益曾在新嘉驿见到会稽女子的题壁诗,并各有唱和诗三首。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八《题会稽女子诗跋》记录了此题壁诗,并写道:“予览之不觉泫然,犹冀其未必死也,因作三诗书其后。”钱谦益的唱和诗见于《牧斋初学集》卷二,题为《新嘉驿壁和袁三小修题会稽女子诗》。此时,明代文学大家冯梦龙,把“会稽女子”收入《情史类略》卷十四“情仇”,题作《驿亭女子》,曰:“女子不知何许人,其诗与叙见于新嘉驿壁”,并按原韵各和了三首诗。
曾官任山东提学佥事的清初诗人施闰章,在《蠖斋诗话》中写有《新嘉驿女子诗》一文,记载到:“驿在滋阳县北四十里,池台古柏,剧有幽致。驿后土壁,故会稽女子题诗处。诗传于世,而驿壁字无存者。余至询之,有老驿卒秦登科年七十矣,能诵其诗。”直至清代,对会稽女子的题诗,仍不断有人悼和。除施闰章之外,还有广陵赵开雍、太原张淑、山阴张文钦、高邑李皋等人也有诗作传世。
在知识女性的唱和方面,除前述柔嘉的《和会稽女子》之外,清人徐釚撰《本事诗》后集卷七中记载了湖广女子畹兰女士的《悼会稽女子》(二首),诗曰:“多情况有千秋月,夜夜墙头照墨痕”;清人沈季友辑《槜李诗系》卷三十四中记载了长春姐的《和会稽女子驿亭》(二首),诗曰:“青灯此夕怜孤影,何事天涯不泪垂”,两人均表达了对于会稽女子的怜悯之情,引发对自身遭遇的强烈共鸣。
会稽女子题壁诗的创作,丰富了古代驿站传播的功能和体系,驿站类公共社交场所、文化场所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得以突显,驿站文学的创作保存、交流传播、品评鉴赏都与它密切相关。因此,对驿站文学研究在关注时间维度的同时,也要关注其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地理学”概念,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对驿站文学给予关注,有助于感受作家创作的现场氛围,贴近更为真实的社会境况。
六、时空双维———新嘉驿女子题壁诗的文化言说
新嘉驿女子题壁诗催生于新嘉驿这一运河驿站,是明清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产物。可以说,该题壁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映射出了明清时期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可以窥见到明清两代的社会状况、女子教育、文坛景象;在空间维度上,则可以思考运河驿站对社会文化产生、发展及传播的积极影响,甚至可以将视野延伸到“大运河”这个更大空间形态,追溯明清大运河发展所带来的交通便利以及周边城市人文社会的繁荣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时空双维给予我们对于新嘉驿女子题壁诗的认知不是孤立单列的,而是彼此交互的。
关于时空双维下的文学鉴赏,朱寿桐论述到,“人们对空间物象的审美感受往往表现出趋异性,而对于时间形态的审美感受则常常体现出认同感”,在空间上,“文学家常常对陌生的地理风貌有一种难以抵挡的新鲜感和难以遏抑的歌唱欲”;在时间上,“记旧的情结属于时间的感性,面对时间维度,每个人都有回不去的故乡”。依朱寿桐所言,人们的审美感受在时间维度上求同,在空间维度上则趋异。
正是在这种“求同”“趋异”的作用之下,新嘉驿女子题壁诗才成为如此独特的存在。会稽女子题壁前首先言明“生于会稽”,灯下独泣之时难免生出思乡之情,而这种情感对于过此驿站之人是共有的,即使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亦有撩拨思乡之感,这就是求同。会稽女子受正妻压迫“非一日之寒”,然于新嘉驿小憩,异地异景,情感瞬间爆发,再难自抑,便将一腔情愫全部倾注于新嘉驿驿壁之上,这便是趋异。同样,对于新嘉驿女子题壁诗的读者、和者而言,由人及己,不免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是在“趋异”中品读与唱和。
时间在变,空间也在变。与成于纸墨、留存书史的诗作相比,题壁诗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是因为,墙壁破损、驿址变迁等空间破坏或移动极易造成题壁诗被毁,从此葬于瓦砾,声销迹灭。这也是为何明清文人十分热衷收集整理女子题壁诗的原因之一。段继红对此论述到,“一首女子题壁诗能使明清两代文人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不能不说微妙复杂,在这种琐碎的整理和考据之中……还有着他们保存即将消亡之文化的良知。”另一方面,运河驿站开放性、流动性的空间特点,也造就了新嘉驿女子题壁诗易于被更多过往的旅客熟知和传播。由此可见,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一经发现便蜚声诗坛,与新嘉驿这一地理空间有着不可规避的关系。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成为研究界的一股热潮,甚至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种时尚。运河驿站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备了“驿站”“大运河”等地理空间的言说维度,将其纳入文学地理学进行解读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可以说,运河驿站诗的“文学地理”特质为我们更多维、更全面地了解大运河地域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运河、驿站、文人、诗作共同构建起一个有“情”有“理”的文化言说空间,为挖掘不同时空的大运河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者:张伟 王占一